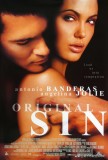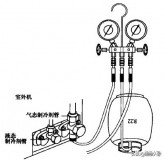【编者按】今年1月初,姚路来到刚刚开放旅游签证三个月的沙特阿拉伯,做了近一个月的深度旅行。结束首都利雅得的现代化五光十色后,她来到沙漠,探访最传统的贝都因人生活。
出发去塔布克(Tabuk)的那天上午,沙发主哈桑给我发来了一张装满睡袋、帐篷、各种工具和物资的皮卡车照片,告诉我:“露营的装备都准备好了,就等你来了。”
我在大巴上睡了一觉,醒来时正值夕阳。窗外依然是没有起伏、一成不变、苍凉荒芜的沙漠,连T.E.劳伦斯也承认这里生活的艰辛:“几年来,我们与其他人住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中,呆在无情的苍穹下。白天,烈日蒸灼我们,强风把我们鞭笞得头晕目眩,夜晚,露珠沾渍我们,沉默的满天繁星让我们瑟缩得无比渺小。”
此刻,强风正鞭笞大地,细细的沙子在空中飞舞。在落日余晖的照耀下,空气仿佛穿上了一层金色的薄纱。我们的大巴就这么缓慢地、艰难地穿过一层层沙幕,在日落前,抵达了靠近约旦的沙特西北部城市——塔布克。
哈桑开着皮卡车到车站接上我之后,就径直离开市区,去他那距离市区65公里的沙漠营地了。
贝都因式的露营生活
即使身处城市,我已经能感受到露营的氛围了,因为路边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售卖柴火的小贩。哈桑告诉我:“冬天,塔布克的许多居民都会去沙漠的营地欢度周末,有时与家人、有时与朋友。我每个周末都会和朋友们去沙漠的帐篷聚会、聊天。”说着,他也在一个摊贩前停下车,买了一捆柴火。
皮卡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漆黑的夜色中,一些LED灯勾勒出一个个帐篷的模样。
哈桑的营地并不在沙漠深处,实际上,它就在高速公路边。他的营地规模很大,有三个帐篷区域,一个用于朋友聚会,一个用于家庭聚会,一个用于公司聚会。我们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哈桑停稳车后,打开引擎盖,接上电瓶和电线,再发动车子,用来取电照明。

哈桑的营地规模很大 本文图均为 姚璐 摄
冬天的夜晚,沙漠的温度只有零度左右,前些日子,这里还下过一场几十年一遇的大雪。照看营地的佣人——来自苏丹的默罕默德——拿来一件贝都因厚长袍给我披上,然后和哈桑一起,把皮卡车里的各种物资搬进帐篷。
哈桑的传统贝都因毛毡帐虽然是营地里最小的帐篷,但依然很大,容纳20个人绰绰有余。帐篷中间有一个火炉,火炉边摆着烧水壶、茶壶和咖啡壶。几块花色的阿拉伯垫子围绕着火炉铺在帐篷中央,每隔几个空位还有一个扶手。似乎只要再来几个身着传统服饰的贝都因人席地而坐,就变成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中的场景了。
哈桑忙前忙后搬东西进帐篷的同时,不忘给我展示他的各种露营装备。他拿出一个水龙头,接在水管上,插到沙子里,就成了随时可以方便取用的“自来水”;他甚至还从车里搬出了一个带扶手和靠背的单人沙发,说这是给我的“酋长宝座”;他有锅碗瓢盆一应俱全的炊具包、调味料包,还有工具包、急救包,甚至有个装着各种咖啡粉、咖啡豆和研磨咖啡全套装备的大包。
他说:“有时我会一个人去沙漠里露营好几天,所以我习惯到哪都把所有东西带上。”

帐篷内部有火炉、地毯和坐垫,哈桑还为我准备了一个“酋长宝座”
我刚刚坐定,哈桑就拿来了一个冒着烟的熏香炉(Mabkhara)。这是贝都因男人亘古不变的见面传统礼仪:主人拿出燃烧着乌木(Oud)的香炉,身着传统阿拉伯长袍的客人用头巾轻轻包裹住香炉,让香味顺着头巾蔓延到全身。我没有头巾,就凑近香炉、用手轻轻扇动烟雾,以示谢意。
随后,哈桑一边给我倒阿拉伯咖啡,一边说:“你知道吗?贝都因人在为你送上阿拉伯咖啡前,自己会先喝一杯,证明没毒。”说罢,他给自己倒了一小杯,一饮而尽,开玩笑说:“你看,我已经喝了,没毒。”
记得第一次在沙特喝阿拉伯咖啡时,我惊叹道:“这真的是咖啡吗?”这种咖啡,与我们所熟知的咖啡,在香味、口感和味道上有着天壤之别。作为世界上最早种植和饮用咖啡的地区,沙特人至今仍然饮用最老式的生豆烘焙研磨烹煮的咖啡,并配以豆蔻、肉桂、茴香、丁香等香料进行调味,也不会把咖啡渣滤掉。对我来说,它比一般的咖啡更清淡、清爽。
在沙特,阿拉伯咖啡的饮用方法很像喝茶。通常来说,主人或主人的佣人会不断为客人添加咖啡,如果你不想喝了,可以摇一摇手上的咖啡杯、或将咖啡杯倒扣放在一边,以示礼貌回绝。
与阿拉伯咖啡同时被端上来的,是各式各样的椰枣。椰枣是贝都因人最依赖的食物,它稠腻的口感、超高的甜度,可以让人迅速补充能量。再加上易于保存和携带,椰枣毫无疑问是与骆驼同样重要的沙漠生存必需品。
在沙特旅行,只要与本地人同吃同住,每天几乎都要吃上好几次椰枣。哈桑拿出几个装着不同椰枣的罐子,给我介绍它们不同的产地和口感。有的椰枣特别干涩,像是晒干的果脯,味道没那么甜;有的特别黏稠,像刚刚在糖水里泡过一样。过分甜腻的椰枣,搭配有点苦涩的阿拉伯咖啡,味道上正好中和、相得益彰。
哈桑休息了一会后,拿出一个装着面饼的塑料袋,开始准备烤面包。他笑笑说:“贝都因人的做法是把揉好的面饼埋入柴火灰烬中煨熟,然后抖掉灰尘。但我们用的是现代化的方法。”
他拿出一个饼铛,把它烧热后,往上面浇点水。等水蒸发干净,他用手把面饼铺到饼铛上,然后倒扣着放在火炉上烘烤。渐渐地,面包的香味弥漫在帐篷里,让人垂涎欲滴。等一面烤得差不多后,哈桑用铲子把面包翻了个面,动作和我们铲杂粮煎饼时一模一样,看得我直乐,心想:世界各地人民的烹饪智慧有时真是异曲同工。
一会儿,一个香喷喷的面包出炉了。哪怕没有任何调味,面粉自身的香气和口感,就已经足以慰藉这沙漠中的寒夜。

正在烘烤的面包
晚饭后,我在依然飘荡着面包香气的帐篷里躺下。结实的毛毡帐篷挡去了夜晚的寒风,高速公路上也终于不再有车辆经过。在这个几乎没有任何声音打扰的沙漠之夜,只有繁星静静地笼罩着大地。
红色沙漠之旅
我本没有对沙特的沙漠报什么期望,毕竟一路从东部城市达曼走来,我的旅程已经延续了十几天,目之所及都是平淡的、毫无生气的、千篇一律的黄色沙漠。
但第二天,当吃完早餐走出帐篷,我就知道不虚此行了。眼前的红色沙粒被晨光照耀得格外温柔细腻,高大俊俏的怪石屹立在一望无际的沙丘之上。这像极了《火星救援》的场景,和深受我喜爱的约旦月亮峡谷简直异曲同工。哈桑也附和了我的观点,说:“是的,这里离约旦很近,地貌上很像。约旦那一侧的沙漠叫Wadi Rum(即月亮峡谷),我们现在所在的叫Wadi Dum。”说着,他打开那存储了上百条沙漠越野线路的导航,说:“我们的沙漠之旅要开始了。”
我们只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一会,就径直拐入了火红的沙漠。沙漠里没有明显的车轮轧过的痕迹,像是一片从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哈桑一会把我带到峡谷之上,俯瞰深深的沟壑;一会带我爬上沙漠的制高点,瞭望无垠的沙海……我手脚并用地爬上各种岩石顶端,独自沉浸在红色沙漠火热的色彩和无边无际的辽阔之中。

红色沙漠
接近中午时,哈桑开始减速,东张西望。他开到一片有零星灌木丛的沙漠,下车出去,捡起一些枯了的枝条,对我说:“我要找一些可以用来燃烧的枯枝,等会烤面包用。”我帮他一起四处寻找,但他一再叮嘱我:“只能找枯了的,不能找还在生长中的,这是沙漠的规矩。我们不杀雌性动物,不砍绿色的植物。”
我们把捡来的枯枝放到皮卡车的后斗,就驱车前往哈桑的“秘密基地”了。
这是一个类似于“一线天”的谷底,可以完美地躲避沙漠的狂风。入口处有一棵很大的树,像是一面旗帜,向沙漠中想要小憩的人们招手示意。
哈桑查看了一番“秘密基地”,高兴地说:“这里还有上一波人留下的炭灰!太好了!”我正好奇炭灰有什么好的时候,哈桑继续解释道:“因为这种炭灰下面还是燃烧着的,我们很容易生火。”
生火后,哈桑在火堆附近铺上地布,搬出给我准备的沙发,把茶壶和咖啡壶架在一个三角形的简易“灶台”上,开始烧水,同时又拿出和好的面粉,准备烤面包。

惬意的“午休”
“秘密基地”照不到太阳,算得上沙漠里绝佳的天然休息场所,但冬天的背阴处有点冷,好在火堆近在咫尺。我喝着刚煮好的红茶,一边伸手烤火,一边看哈桑如法炮制地烤面包。沙漠寂静得只剩下茶壶里的水冒泡的声音。捡来的枯枝有股神秘的清香,仿佛能安抚神经,我和哈桑在这空无一人的沙漠沟壑里,吃着香喷喷的面包,喝着咖啡,相对无言,享受着残酷的沙漠生活里难得的片刻安宁。
营地聚会
休息片刻后,我们收拾东西、开车回到营地。这时,哈桑的几个朋友已经围坐在帐篷里了。他们起身与我一一问好后,一个不知从哪冒出来的小男孩为我倒了一杯咖啡,并把一份椰枣放在我的面前。
阿拉伯人喜好群居,男人们总是穿梭于各种各样的聚会,哈桑和他的朋友们也不例外。一束阳光从帐篷顶的小窗户倾泻下来,大家借着这光亮,围坐在火炉边,用阿拉伯语谈天说地。劳伦斯写道:“对一般的阿拉伯人而言,火炉就是一所大学,他们在火炉旁生活,与族人闲聊,听他们部落的新鲜事、诗歌、历史、爱情故事、争讼、交易。他们从小在火炉旁闲聊,使他们长大后勇于表达意见,辩才无碍,可以在各种聚会中侃侃而谈。”

聚会现场
这天正是中国的除夕。我坐在正对着门口的位置,看着炉火生生不息,烟雾升腾。可以想见,在遥远的过去,沙漠烈阳当头、劲风呼啸,一顶能遮阳的帐篷、火炉边的茶水和新鲜出炉的面包,才可以给人在动荡艰辛的生活中,带来一点点极其有限却又必不可少的安宁和舒适。
而我没想到的是,如今的沙特那么现代化、那么有钱,人们却还是如此迷恋古老的生活和社交方式,几十年如一日地把周末的时间献给沙漠和帐篷,并乐在其中。
米饭的香味把我从神游中拉回现实,哈桑的佣人默罕默德端来了两个装满米饭和鸡肉的大盆。所有人围着大盆坐下,直接用手抓起米饭往嘴里塞。哈桑吃了几口,看到一脸困惑的我,才恍然大悟地对默罕默德说:“拿一个勺子。”
我不甘心与众不同,想学习他们用手抓饭的技巧。哈桑边演示边告诉我:“把一些米饭拨到自己面前,用手指头而不是手掌,把他们用力捏起来,然后就像吃饭团一样,把它塞进嘴里。”他熟练地往嘴里送着“饭团”,而我却怎么也没法让米粒听话地团结起来,最终只能放弃,用勺子吃了起来。
这种米饭配鸡肉的料理,叫做Mandi,是沙特的特色。单从烹饪手法和味道上来说,它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可是在大部分时候只能吃干面包和椰枣的沙漠里,米饭就显得格外香甜可口,而米饭上的鸡肉,更是所有人争抢的目标。

超大份的Mandi
饭后,一个肤色黝黑的苏丹人正牵着几只骆驼路过帐篷,哈桑赶紧招呼我出去看。沙特人谈起骆驼,总是一脸宠爱,因为被称为“沙漠之舟”的骆驼是找水专家,任凭沙海茫茫,骄阳似火,酷热难耐,单峰骆驼却从不会迷失方向。
哈桑说:“骆驼可以12天不喝水,又能驮很多东西,在沙漠里,它们比皮卡车和GPS更可靠。”更何况,骆驼一身都是宝:驼奶可解渴,驼肉可充饥,驼皮可做衣服,驼毛可做帐篷,驼粪可做燃料,连驼尿都可以当生发头油。在沙漠里,骆驼是人类必不可少的好伙伴。
如今,沙特人喜欢雇佣苏丹人为他们照看骆驼和帐篷。这些苏丹人一贫如洗,双手粗糙,做一切体力劳动。哈桑的佣人——来自苏丹的默罕默德,终日住在营地的一个小帐篷里,照料帐篷,为哈桑和他的客人准备餐食。有时,哈桑会招呼默罕穆德一起入席喝茶,他总是腼腆地推辞一番,似乎时刻不忘自己的身份。直到抵不过哈桑的劝说,才憨厚地挑一个最不舒服的位置坐下,一边频繁地替大家添茶倒水,一边趁着间隙自己也小酌一点。
日落时分,我催着哈桑和他的朋友一起开车去拍摄日落。沙漠被夕阳照得通红,似乎下一秒就要燃烧起来。我兴奋地下车,想要向前,却被哈桑喝止:“别往前走,别破坏了沙漠的纹路。”说着,他和他的朋友都蹲在了原地。我顺着细沙汇聚的方向望去,一尊如“雄狮”般的石头孤独地屹立在红色沙海上,如同沙漠之王,静静注视着远方。
哈桑和他的朋友正兴奋地拍个不停,我想,沙漠就像大海,他们就像海里的鱼,注定永远也无法割舍对这片沙漠的依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