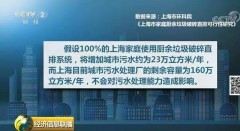【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聆雨子】
2011年,《建党伟业》的结尾,一大代表们在南湖的画舫里抱作一团、泪流满面地高唱《国际歌》并朗诵《共产党宣言》,在船头,周迅饰演的王会悟撑着一把油纸伞款款起身、缓缓回头、露出一个不可方物的微笑,云开雨霁,那身影恍若女神。
2021年,《1921》的结尾,一大代表们在南湖的画舫里抱作一团、泪流满面地高唱《国际歌》并朗诵《共产党宣言》,在船头,倪妮饰演的王会悟撑着一把油纸伞款款起身、缓缓回头、露出一个不可方物的微笑,云开雨霁,那身影恍若女神。
十年时间,两部电影,在高潮部分的落幅画面里,竟用了几乎复制黏贴的镜头语言。
哪怕它们出自同一个导演(黄建新,当然,他在两部电影里都只是“联合执导”之一)、聚焦同一历史事件,这种高度重合依然十分罕见。
无独有偶,同为2021年7月1日上映的《革命者》,张颂文饰演的李大钊和秦昊饰演的陈独秀在一场决定“要彻底改变这个世界”的对话戏里,边吃着涮羊肉火锅边聊,而且,不知是巧合还是故意设计,鸳鸯锅辣味的那一半对着外向的陈独秀、不辣的那一半对着沉稳的李大钊——一切细节,又和《建党伟业》里一模一样。

《革命者》和《1921》两部电影7月1日上映(图片来源:1905电影网)
政论、历史和剧情:不同阶段的不同任务承担
我们大概可以将上面的奇特现象,称为“经典文本的隐形渗透与惯性复现”:对类似题材的反复演绎过程里,前后相继、经验叠加、彼此借鉴,以往某个标杆式的处理珠玉在前,让后来者情不自禁地、甚至是下意识地沿用了其中的某些范型。
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对于中国电影而言,“建党”是一个被“反复演绎”的大IP,是一份“群体记忆”,是一种可以产生“惯性复现”与“隐形渗透”的“经典文本”。
从《建党伟业》到《1921》,还要加上更早之前的《开天辟地》(1991年黄亚洲编剧、李歇浦导演),正好分属于上世纪到本世纪的每一个十年,“前后相继、经验叠加、彼此借鉴”,重大献礼类主旋律电影的象征性依旧,而其表现性则日益多元多样。
因为是主旋律,因为是重大献礼,这条路除了艺术和技术的因袭,还多了一份精神传承的味道。这条路理应会在建党百年到达一个里程碑,也理应获得思路梳理、经验总结、价值评估。
毕竟,我们刚迎来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七一档”——第一个由“重大献礼类主旋律电影”撑起的档期。要知道,在那之前,“档期”一直都是个纯商业概念。
从所涉及历史时区的长短来看,上述三部电影,分别是“中景-全景-近景”的差异:《开天辟地》以建党两年前的五四现场切入,《建党伟业》自清末和辛亥娓娓道来,《1921》则文如其名——凝练在一年(1921),凝练在一地(上海),凝练在一事(开会)。
这些选择各有道理,因为它们本身就反映了不同的创作要求:
《开天辟地》回答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这个问题,所以它要从最切近的“为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的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开始。

《开天辟地》官方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建党伟业》回答的是“为什么要建党”这个问题,所以它的整个结构就是先向大家展示“什么路都走不通”,然后再来到“这条路”上——“试错”的过程,构成它的主体部分。
对《1921》而言,前两个问题都已经是社会共识,它回答的是“要怎么建党”这个问题,是方法论上的艰难和勇敢,于是它直接把自己放在那个具体的时刻,一开篇的对白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组织”。
一个是what,一个是why,一个是how。
《开天辟地》是上世纪国营片厂时代那些大制作的标准风格:相当写实的“准文献纪录片”,朴拙、严肃、端方正直,时时着眼于理论的探讨,一上来就是李大钊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论争,后面还出现了共产党人与无政府主义的分野、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辩论。
《建党伟业》像是在电影作为公共文化消费品的渠道下沉和受众普及背景下,用更广阔的视野,把“完整地交代历史知识”摆在最前,拍出一部视觉版教科书。
《1921》又不一样。黄建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建党伟业》(的任务)是点状的,出现了两个点就没了,而《1921》有从始至终贯穿的人物来衔接故事。”有了人物就会有情感关系、工作关系,有了故事,电影就会开始在情节上发生转折和冲突。

黄建新导演(图片来源:新华社)
注意,人物、故事、情节,这些看起来暂时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的、隶属于电影本身的词汇,构成了《1921》的关键——很快我们还会讲到,它们,甚至构成了当前主旋律电影发展新方向上的关键。
那么,要为三者下定义,不妨概括为:政论片-历史片-剧情片。这三个片种,恰恰是建党题材一路走来时,对自己所置身的不同时代、所肩负的不同文化使命,所做出的不同回应。
当然,“历史片”和“政论片”,也并没有在建党题材里,失去它们的当代价值:
《1921》依然围绕着“来自不同地域的不同代表分别经历了什么”,做出了很多辅线性前文本,让时间形成历史性的立体散射,更不用说,它在片头和片尾用大量黑白真实镜头所补充交代的中国革命简史。
而同时上映的《革命者》,虽然是一部焦点更加明确的传记片(浓缩于李大钊一人),且用了文艺片的叙述思路——打乱时间线的碎化剪辑、随时建立过去和现在的互文关系,但其实,它非常侧重政论:在它的每一次非线性闪回里,都对应着一次政论式的碰撞、试验、争锋和实践——李大钊和陈独秀之间、和孙中山之间、和蒋介石之间、和毛泽东之间、和张学良之间、和底层民众之间……
主旋律的类型化、鲜活化和趣味化
很多观众心里,“主旋律”往往是敬而远之的代名词,因为这个序列确实出过许多政治上很过硬、但诠释形态过于公式化图解化简单化脸谱化的作品,更勿论“建党”这样主旋律中的主旋律。
怎么把它与电影艺术当前所达成的最先进的叙事抒情手段相结合,怎么在已经高度成熟和发达的现代电影工业程序里,放进我们自己的信仰、人物和故事——让主旋律与类型片交融,这是必由之路,也是大势所趋。
应该看到,它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些年,“主旋律电影类型化”的边界不断拓展,《红海行动》是战争片类型,《我和我的家乡》是喜剧片类型,《中国机长》是灾难片类型,《战狼》系列甚至是超级英雄片类型,《建军大业》甚至是热血偶像片类型。

《红海行动》
在诸多类型里,谍战又是和主旋律合作得特别成功的一个:往远了讲,有《一双绣花鞋》、《永不消逝的电波》、《夜幕下的哈尔滨》,往近了说,有《暗算》、《潜伏》、《红色》、《伪装者》和前不久的《悬崖之上》,部部都是红色经典。
《1921》也试图诉诸谍战。来自日本特高科和来自共产国际特派员的两条线,让故事在很长的时段里保持着一种侦缉与反侦缉的、猫鼠游戏式的类型元素:
更名、化妆、接头暗号、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甚至还有追车戏,而且拍得非常新颖,还利用了老上海街头特有的公共交通工具(巧合的是,《革命者》里北京游乐场里一场利用哈哈镜面拍出的躲藏和捉捕戏同样非常新颖,它们都体现出了当前主旋律里的匠心设计)。

《1921》截图(图片来源:1905电影网)
类型片里的关键,除了故事,还有视点,以及人物。
《1921》使用的是不多见的“侧向视点和侧方叙事”,线索人物既没有落在李大钊陈独秀两位巨头身上,也没有落在毛泽东这位后来的领袖身上,而是落在了李达和王会悟这对夫妇身上——因为他们是会议的组织操办者,用个时髦的形容,他们是“会务组”——他们仿佛“有参与度的现场观众”,保持了一份主观视角的始终在场。
《革命者》则用了“多声部混叠”,以李大钊被害前38小时为主要时间线,通过一系列关系人物的回忆,为主人公立起了革命者、人师、人夫、人父的多重角色。
《1921》很重视用细节来暗示人物未来的选择,所以周佛海陈公博已经显得怯懦而虚荣,所以当这些年轻人在停电的陋室里挑灯夜谈中国的出路时,另几个年轻人(蒋介石与陈果夫)却在挥金如土的证券市场主宰一次豪赌游戏——镜像般的对偶,如春秋笔法式一字定褒贬。
《1921》又并不避讳那些出色的人物曾经的迷茫和困惑,甚至是他们产生过的错误判断,于是,他们会争执、会发生冲突、会焦虑、也会偶尔有一点自我怀疑。
《1921》也不介意让他们变得很有意思、很逗趣:何叔衡刚到上海那一路看西洋镜般的兴奋;毛泽东与杨开慧告别时何叔衡的电灯泡尴尬;王会悟练习说谎前先跑步;毛泽东会因为饭桌上没有辣菜而哀叹“湖南完咯”。
这都是鲜活,作为承载物和诠释物的人,作为媒介和触点的人,一旦能鲜活起来,宏大叙事就能够“落地”、以及更进一步“落入人心”。

《1921》截图(图片来源:1905电影网)
当然,在这些丰富性里,我们也要看到某种短缺性,某种因为丰富性而造成的凌乱:
《1921》在党史线和故事线之间仍旧存在相对的脱节,前面所说的谍战戏码,有时更像粘在建党周边的一个“上海大追击”特别番外篇。
至于《革命者》,想把高潮以时间轴的一点一点逼近而带起来,其实也没有完全起到效果。
毕竟,因为谁都知道一大最终顺利召开,类型要素里某些最核心的东西——比如悬疑,等于提前失去了,这造成了太大的客观难度。
综上所述,建党题材,或者说更广义的主旋律,已经找到了恰当的发展规律和模式,以扩大自身的感染力和可看性,只不过,在具体的前进过程里,还有一些难免的经验不足、难免的磕磕绊绊。
毕竟,这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不必因为一点波折与瑕疵,去怀疑前路的光明。
青春化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说主旋律的类型化是一种已持续多年的、也基本可视作成功的趋势,那么主旋律的青春化,就是一种出现得更加晚近、也更有争议的新现象。
首先必须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所说的青春化,不等于偶像化与饭圈化,没有人规定过,青春就只有后面那几样。
一切只取决于,有没有恰切的情感公约数,来建立起主旋律和青春之间的情感共同体。
目前来看,青春化大致包括内外两部分:“内”指情绪上的青春热血、表达上的浪漫和肆意;“外”指使用青春偶像担纲主演。
“内”的部分当然是成立的。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年轻人试图做大事”的时代。《1921》为每个出场的人物都标注了年龄,这让我们意识到,他们原来都这么青春,就连作为他们老师和老前辈的李大钊,也都不过才29岁。
他们也是80后和90后——19世纪的80后和90后。他们的勇敢、决绝、坚定不移、百折不挠,他们对光明未来的追寻,都是青葱岁月的一部分。他们搁在当时的中年人眼里,也不过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不安分念书做工当官赚钱、满脑子胡思乱想的混小子。
李达夫妇在屋顶唱国际歌、李达熬夜工作后爬上屋顶拥抱太阳、何叔衡深夜落泪讲述参加革命的缘由,还有毛泽东在霓虹和烟火下的纵情飞奔,这些都是标准的“青春片”的拍法。

他们配得上这种青春化叙事,那个时代里那一份燃爆了的挺身而出,那个初升旭日般年轻的党,和她正在揭开的少年中国,也配得上这种青春化叙事。
更何况,青春还在代际之间嬗递,向着更年轻的一代又一代,这才有李达夫妇住所对面窗户里的小女孩,才有片尾参观一大会址的那一批批小学生。
而“外”的部分,情况就有点复杂。《1921》在曝出选角名单时,就引发过一轮争议。
“流量”和“伟人”之间,确实形同天堑。而且,一旦大批爱豆带着偶像包袱进组,人人都要获得足够的镜头和戏份,客观上会造成一个本就枝蔓迭出的题材,变得愈发杂沓破碎。
但也要看到,在“谁来饰演伟人”这道门槛上,中国影视的标准本就是逐渐放宽放活的。比如毛泽东,最初是特型演员的专属(古月、王霙、侯京健这老中青三代),后来有了唐国强这样本身不是特型演员、却因多次成功扮演、活生生把自己变成了特型演员的案例,再后来,还有刘烨、谷智鑫等其他中生代演员的出色表现。既然这样,王仁君和李易峰的尝试,也没有什么可诧异的。
当然,演伟人本身意味着一种更高的要求:无论对演技,还是对人格(因此有过污点的艺人必然不在考虑之列)。那反过来说,这样的体验,也是让年轻一辈演员获得精神洗礼和升华的最佳机遇。
而且,他们未必没有他们的优势:王仁君就谈及“导演不希望毛泽东主席后来在思想上的成长、高瞻远瞩和领导经验代入到他的青年时期”,还原青年状态、不把他后面的性格和特征完全带到前面来,“没演过的人”反而能摆脱先入为主的包袱。
如果我们把成功诠释伟人的考评要素从单一的“形”的肖似,推入“得神忘形”的境界,那“他长那样怎么可以演领袖”压根就成了个伪命题,更不必讲像周恩来那样,当初本来就有超高颜值。
总之,发挥年龄优势,深入洞悉这些伟大人物年轻时的心灵源动力来自哪里、他们身上的少年感和理想之间的关系,发挥号召力优势,让更多年轻观众加入这份精神共振当中。
这样,就不至于让这类影片最吸引人的地方,永远停留在卡司阵容上,也不至于让这类影片激起的热议,永远充斥于“我家哥哥好帅”上。
这就是我们对“青春化”叙事的态度:在“道”的问题上,它是拥有合法性的、是不必去苛责与怀疑的,而在“度”的问题上,它是需要斟酌、需要进一步规范和严谨对待的。
理性看待前者、认真琢磨后者,此为正道。
不要忘记,今年建党纪念活动各色宣传海报上的标语,写的正是:“一百年,正青春”。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