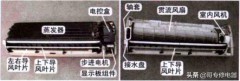2022年2月20日刊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思潮,一代人有一代人之焦虑。虽然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但在家庭剧里,我们总能最大程度地找到有关生活的共鸣。
从《渴望》到《人世间》,国产家庭剧已走过三十多年的光景。这三十年间,社会巨变,传统家庭剧逐渐退场,新的家庭剧开始登台。家庭剧的创作风格随着时间改变,而影像本身似乎也在影响着它的观剧人群。
家庭剧的两次转向
诗经有云: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家庭,是国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正因为如此,自有电视剧起,便有家庭剧存在。
最早的家庭剧,指的就是单纯的家庭伦理剧。
这一时期的作品,以室内剧为主,最典型的即是《渴望》。彼时,我国城镇化建设刚刚兴起,商品经济热潮涌动。传统价值观受到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影视剧从农村苦情剧向城市情感剧演进。观众在刘慧芳身上,完成了对善的寻找。

21世纪初的国产家庭伦理剧延续着这一模式,涌现出了《空镜子》《亲情树》《搭错车》等一批佳作。它们把伦理纠葛放置在开放的社会场域中去讨论,透过家庭成员的悲欢离合,表现大时代转向里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精神风貌。
第一次转向很快到来了。那些表现特定社会背景下人物坎坷命运的作品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婚姻这一狭隘空间中,更加隐私的个人话题和两性关系。
于这一阶段的影视剧而言,家庭只是拍摄主体,亲情伦理撕扯才是戏剧重心。比如,人到中年的半路夫妻,收养抱养孩子又老来得子,父亲去世子女与后妈的纷争,以及家庭伦理剧中最经典的永恒命题:婆媳关系。

《渴望》中那个完美无瑕的“刘慧芳”,在流淌的时光沙漏旁缓缓改变模样,成了《双面胶》里与婆婆斗个不停的“胡丽鹃”,成了《媳妇是怎样炼成的》里对新家庭力不从心的彭俏俏,成了《金太郎的幸福生活》里的米小米。
但过多同质化的类型剧,也让这时期的家庭剧变得乏味。
不论打开哪个台,讲的都是大差不差的东西。所有故事的重心,都在一条路上奔驰:恶婆婆与小媳妇,强势岳母与无能女婿,和永恒的城乡差异。
这些雷同的情节,脸谱的人物,使得观众审美疲劳。于是,转向再度开始。这一次,家庭的母本被重塑,伦理的框架被拆解。传承已久的亲情伦理讨论,被数不胜数的社会焦虑所取代。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焦虑,成了家庭剧的新主流。

不论是《小别离》《都挺好》还是《小舍得》《小敏家》,都不再围绕原始的夫妻关系做文章。哪怕讲家庭,讲的也是更复杂的情感迷惘:原生家庭创伤、亲子代际交往、不同阶级家庭的相处,从“小家焦虑”转向了“社会焦虑”。
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除了“中产”阶级家庭掌握了更大程度的发声权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飞速发展的时代让一切趋于定型。《双面胶》的基本矛盾,是来自农村的婆婆和当地土著儿媳的观念不合。在当时看来,这种冲突很合理。
现在再拍这种剧,就有点不合时宜。2007年毕业的大学生,掏空家底还能留在上海。2022年毕业的大学生,几无可能。更别提和当地人结婚了。小家都组不成了,自然不存在小家焦虑。该给买得起房的人拍拍孩子了。
争议中的新家庭剧
不过,即使戏剧主题从婆媳之争转到了社会焦虑,观众似乎依旧没有被满足。《都挺好》也好,《小舍得》也罢,热播期间有一个词屡屡被提及:狗血。
难道说,编剧离开了“洒狗血”就不会讲故事了?还是说,越狗血的作品观众越爱看?

必须承认,如今的观众不仅喜欢过自己的生活,还喜欢在荧屏上看“生活”。这是家庭伦理剧的定位:将那些最戳人心的生活“血淋淋”地放在观众面前。
何为狗血?这个问题,得放到具体实例中找答案。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洒狗血”似乎是韩剧的专用名词。如果说,琼瑶剧造的是一场关乎爱情的浪漫幻梦;那么,韩剧就是把各种令你淌泪的情节攒在一起,用绝症、车祸和复仇三件套,搭配上悲情BGM来给你“致郁一击”。
从当年的《蓝色生死恋》,到去年的《顶楼》;从重生整容后归来复仇的《妻子的诱惑》,到“你出轨我出轨”的《夫妻的世界》;以及“爷爷原来是爸爸”的《优雅的家》、疯狂作死的《皇后的品格》…真真狗血年年洒,年年俱不同。

然而,随着韩剧逐渐向悬疑、惊悚、历史领域多元化发展,观众也将目光回转国产剧。将社会焦虑作为燃料的新家庭剧,成了新的靶子。比如《都挺好》。
一个重男轻女、极度偏心的妈妈;一个回避问题、不闻不问的爸爸;一个奔着自己前程无心无力管家中事情的大哥;一个自私自利、窝囊啃老的二哥;以及一个对家庭冷漠,亲妈去世还在葬礼上打电话处理工作的女儿……
试问,“苏大强”这样的爹搁自己身上,谁不生气、不上头?
然而,非要说国产家庭剧真的越来越狗血了,倒也不尽然。
从某种程度上说,近几年兴起的“新家庭剧”,本就是对当年造成观众审美疲劳的传统伦理剧的一次反击。只不过,屠龙的勇士,再度变成了“恶龙”而已。

如果把目光放长远些,我们可以发现,对家庭剧“狗血”的探讨从未停止过。
以今人之目光看刘慧芳的所作所为,似乎也有点令人难以理解。《人世间》里温婉大方的郑娟,在某些网友口中,已然成了“新时代的刘慧芳”。
事实上,家庭伦理剧的故事发展本就依托狗血推动。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思潮,一代人有一代人之焦虑。经历过的是感同身受,旁观过的是挥洒狗血。
下一部《人世间》在哪?
传统家庭剧逐渐退场,新家庭剧也争议不断,难不成如今的时代,我们不再需要家庭剧了?绝非如此。正如影评人赛人所说,“家庭剧长期以来直至今日,仍是中国电影(影视)的魂魄所在。”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家庭剧仍需在场。
不论口碑如何,家庭剧的热度却稳步在线。《小舍得》在爱奇艺的最高热度突破9000点。和《叛逆者》不相上下。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如今的家庭剧正位于尴尬处境。本质原因是,家庭剧的承受载体“家庭”不再稳定。家庭伦理剧的核心,是在鸡零狗碎、吵吵嚷嚷中保卫家庭,是通过解决问题修补家庭的裂痕,使之更牢固、更稳定以及更幸福。
但如今的家庭剧,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在这些影视作品中,家庭不再与婚姻挂钩,而转变成男人与女人之间不见硝烟的战场。《小敏家》在海报中,直接打出了“婚姻无法定义我们的生活,爱可以”的slogan。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大众的婚恋观发生了变化。
过去十余年来,“爱情”与“家庭”的关系逐渐疏离。一方面,大众依旧对爱情抱有期许之心,但对自我拥有爱情的幻想逐渐破灭。“爱情的确很美好,然而我可能终其一生也无法体味。”正因如此,甜宠剧、磕CP才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家庭的宗法神圣性也遭受了破坏。原本被视为温暖港湾的家庭,如今变成了一种以“平衡式交易”为基准的选择性关系。
正如贝克在《个体化》中谈到的那样,“家庭越来越变成一种选择性关系,变成一种个体的联合,个人把自己的兴趣、利益、经验和打算都纳入家庭,每个个体都得屈从于各种控制、风险和限制。”可以确定的是,传统家庭的定量重要性下降了,丁克、单身、未婚生育等新的生活形式出现了并广为传播。
部分家庭剧的创作者,也不再深入生活。正如邵燕君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所质疑的那样,远离或者从未有过当下底层生活经验(“起于书斋止于书斋的不在场”)的作者能否仅凭道听途说、一腔热情就去为当下的“底层”“代言”?其“代言”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何在?家庭剧也面临这一困境。
其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观众口中的狗血。“狗血驱动”的另一个说法,叫“痛点驱动”。只是,当这种痛点不被认可的时候,嘲讽就会随之而来。
为何会出现痛点与狗血之争呢?根本原因是,唯恐观众不理解自己的主创,以极其刻意的手段,围绕着痛点为观众营造出一种“痛到悬浮”的夸张氛围。不是说,剧中的故事在现实不会发生,而是接连不断发生的概率,几近于零。

观众想要的,是一部思想深刻、自然而然地展现社会问题的影视作品。而主创展现的,是一个刻意的故事,为了人物特意塑造的矛盾,以及过度极端、没有行为逻辑和情感逻辑的纸片人,连带着Bug成为了作品最大的原罪。
这里插句题外话。主创之所以选择这种极致表达,本质上,是主创和观众的诉求不同。或者说,是理解不同。传承了数千年的创作理论,已跟不上如今时代的发展。过去的经典,如今成了套路。过去的戏剧,如今成了狗血。
但观众仍然渴望好的家庭剧出现。去年播出的《乔家的儿女》就收视不错,故事讲述了乔家的五个孩子,在艰苦的岁月里彼此扶持、相依为命的故事。
再比如正在拍摄的由毛晓彤、张俪、李泽锋、王子异主演的《心想事成》,故事以一对都市平凡姐妹最真纯的甜蜜和苦涩,最动人的幸福和忧伤,最渺小又最真切的追求和梦想为焦点 ,展现新时代生活在北京的平凡人的喜怒哀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心想事成》难得地邀请到了张凯丽、孙松共同参演,经典家庭剧《渴望》时隔三十多年再度合体,自然收获了观众满满的期待。

甚至,他们将这份热忱延展到了其他类型剧中。
去年播出的《对手》是谍战剧,正在热播的《人世间》是年代剧。可大众每天在讨论的,还是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相濡以沫、鸡鸣狗跳和一地鸡毛。中年家庭的财政危机、失业危机和子女危机,是《对手》最有戏剧张力的线索。周家人的幸运与不幸,光字片居民的温馨与冷遇,是《人世间》最为动人的细节。

这更像是“家庭 ”。过去我们聊武侠剧,说新武侠剧前途未卜。但不可否认的是,武侠元素已然融入到玄幻、仙侠等颇多类型剧中。家庭剧也是如此,虽然新家庭剧依旧处在一个叫座不叫好的阶段,但“家庭 ”的魅力随处可见。
好的影视作品,应当以情动人。写人物不能只写人性的复杂、纠结,更要写人物关系。写家庭不能只写矛盾、冲突,还要写温暖的抚慰和澎湃的情感。
本世纪初播出的《空镜子》,就潜藏着不动声色的力量。它的戏剧冲突来源于寻常巷陌,它拍出了琐碎生活的温情脉脉。剧中人的悲喜,皆有着实实在在的来处,绝非随意涂抹。杨亚洲导演拍出了生活中多见而荧屏上少见的故事。
广电总局《“十四五”中国电视剧发展规划》指出,创作者应推出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电视剧。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剧仍处在向内求、向外转的关键一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