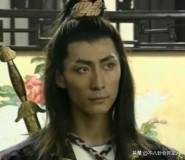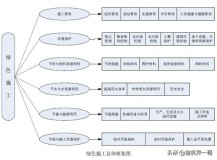中央电视台本属电台一部门
电视演播室设在广播大楼四层东北面拐角处的一个大厅里,大约有 70 多平方米的面积,改造成为演播室。
在演播室的一边隔出一个窄长条,作为导演室,有大玻璃窗能看到演播现场的情况,也可以在导演室里调动摄像机,切换画面,混声、控制音量。在演播室的后面另有一个大房间,里面有两台 35 毫米电影放映机和一台坐式16 毫米电影放映机,放映机面对着墙,墙上贴了一张白纸,算作是电影的银幕,影片就放映在这张纸片上,再用摄像机拍下这张白纸上的电影图像,并把信号播放出去。图像一经播出,电视接收机就可以收看到电影了,但是观众看到的影片与原片不完全相同,因为摄像机拍摄时把影片的边角去掉了。原本国外的设备是放映机与摄像机两机的镜头相对,电影直接放映在摄像机的镜头上,然后播出,无须纸片银幕。但是我们没有这种设备,只好采用摄像机拍纸银幕的土办法,虽然图像效果和画面的完整性受到一定影响,但是能够播出,电视机可以收看电影,也就将就了。
演播室里还有一个像街头老式电话亭一样的小木房子,它有一个隔音的玻璃窗,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问了以后才知道这是播音员的配音室。当放映自己拍的电视新闻无声样片时,放映机发出很强的噪音,为了播音员给影片配音时不把噪音播出去,就搞了这么一个像电话亭一样的东西,权当配音室。把播音员塞进这间“配音室”中, 隔开外面放映机干扰的杂音。这就是襁褓中的中央电视台。
沈力原名丽环
唯一的播音员沈丽环是从总政歌舞团合唱团调来的,她人长得秀丽、端庄、落落大方,声音甜润,口齿伶俐,标准的普通话,简直就是天生的优秀播音员。她没有那种演员的“表演”做派,也没有讨好观众的献媚造作,更没有自视不凡的高傲,她是一个全心为观众服务的好朋友。而且她的工作态度非常好,电视新闻她要解说,全天节目她要串联,她的记忆力非常好,准备稿件的时间短,她竟然全都能背下来,几乎没有发生过差错。这样的播音员真是非常难得的,她的播音名字叫沈力。
众人曾看不起央视
面对电视台不被重视的现状,领导也无能为力,因为那个时候全北京市也没有多少台电视接收机,电视尚不为人所知。哪里像现在,电视是第一大媒体,到哪里拍摄报道,都会受到欢迎。那时候电视台在一些主管宣传的部门那里不受重视,他们眼里报纸第一,新华社第二,广播第三,新影第四。电视台是一个级别很低、可有可无的新闻机构。在宣传领导部门的眼里是这 ——样,更别提老百姓了,老百姓根本看不到电视,甚至连电视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送外国电视台的交换片这么拍
我曾以编辑身份带领一个摄制组去上海拍出国片,摄影是孔令铎、刘贵林,助手是庞亦农、裴玉章。我们在上海不敢住宾馆,因为房价太贵,最后选在南京路原来先施公司后面的一个小旅馆,这里交通方便,价格便宜,但设施简陋,五个人住在一间房里,里面只有一个洗脸盆,没有卫生间,上厕所要到楼下。楼下厕所里面有一个特大的矮木桶,旅客们毫不避讳聚在这里方便,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最奇特的厕所,在国际国内颇享盛誉的大上海,旅店中竟有这种简陋设施,想来十分滑稽,真是大开眼界。
这次我们拍了《越剧皇后——袁雪芬》《上海港》《上海儿童交通公园》《上海无缝钢管厂》四条短纪录片。在《上海港》纪录片中讲述新旧时代对比时,还使用了画面翻转的特技。这些纪录片都顺利审查通过。同时,李华去哈尔滨拍了《动力之乡》,介绍了哈尔滨电机厂、锅炉厂等,叶惠也拍了出国片。
没拍成的白洋淀民风
终于把公社干部等来了,我向他讲了来此地的任务,要拍“冰下捕鱼”“编席”和“采菱”等纪录片,送给外国电视台,并一再说明这是上面交给的政治任务。公社干部倒也爽快,告诉我们“采菱”是拍不到了,因为季节已过,无菱可采,至于其他的内容,县委臧副书记正在这里蹲点,我们可以和他商量,看他有什么意见。于是,他把我们带到臧副书记处。臧副书记指示公社干部陪同我们完成任务,公社干部点头答应。同时他告诉我们冬闲了,农村已经没有人干活了,要搞冰下捕鱼得现组织人力。编席都是妇女干的活,现在的政策是反对妇女搞资本主义,私自编席往外地卖就是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还能不能拍等他和干部们研究研究,然后通知我们。我们一听就凉了半截,拍摄计划 一旦与当地政策相左,任务是很难完成的,若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我们无计可施。
农村的实际情况与我们的宣传大相径庭,作为记者,我们没有报道农村的真实情况,却自欺欺人瞪着眼睛说瞎话,没有的事愣是拍出新闻,说是形势一片大好,这么干还有一点记者的职业道德吗!细细想来不免心中有愧。
先拍手指再拍人
为了便于国内编辑了解画面中的人物,我在拍摄领导人物前先拍自己的左手指,一个手指后拍摄的人是谁,两个手指后拍摄的人是谁,这样编辑看样片时就不会编乱,按照我写的新闻分镜头表编画面,与我写的解说稿才能对得上,解说与画面就不会对错人名。这个方法还是上次去缅甸时孔令铎同志教给我的,不过在缅甸拍摄时极少用到,这次在阿采访拍摄时就用上了。我从阿回国后,剪接告诉我,说我漏拍了一位阿劳动党政治局委员。我一听就急了,不可能,我不相信自己会漏拍,于是和她一起到装样片的篓子前,我伸手就找出那个镜头,证明我没有漏拍而是她漏编了。孔令铎的经验非常管用,采用了这个方法,拍摄时就有了章法,也能避免漏拍。
假镜头新影造
新影厂同志在讨论中,揭发出很多电影厂拍新闻和纪录片时,弄虚作假、劳民伤财的实例。如:拍南方农民在房内活动,屋里比较暗,当地又没有电源,不能使用照明工具,于是就把农民房屋的屋顶拆了,让太阳光照进来;拍县委书记讲话,因为县委书记脸上有疤痕,形象不好看,就把县委书记“换掉”,找另外形象好的人顶替;拍鹰厦铁路时,隧道已经快通了,拍不到隧道开始动工的情形,便在隧道的旁边,再开挖一个新隧道口进行拍摄,代替隧道开始动工的镜头;那张轰动全国鼓吹粮食亩产多少万斤,小孩都能坐在即将收割的麦子上,显示大跃进奇迹的片子是怎么拍出来的呢?原来是摄影师把凳子放在麦田里,让小孩坐在凳子上拍成的。
亲见唐山震后第五天的样子
吉普车就批下来了。我们唐山地震报道小组领了车,立马奔赴唐山,这已经是唐山灾后的第五天了。我们一路向唐山进发。原来的道路和桥梁被震坏了,我们只好向从灾区逃出来的人打听,哪条路可以到唐山。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们哪里的路不通了,可以从什么地方绕过。不断地询问,前行……当暮色降临,我们感觉可能进入了唐山市郊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到达唐山市中心了,只不过再也找不到任何唐山市的标志性建筑物, 四周瓦砾遍布,看不见楼房大厦,没有一栋高过人头的房子,在没有倒地的路灯灯杆下是一排排的死难者,每具尸身上都盖着布或单子,空气中散发着尸体腐败的味道。尸体旁边还有人在守候,他们可能是死者的亲人,没有离开,是在等待安置遇难者,要让亲人入土为安,之后才考虑自己以后的生活。只见逃过死亡的他们,边守护着亲人遗体,边吃着搜寻到的食物,维持自己的生命。
随着大量生命的消逝,一切都停滞了,唐山已经变成一座空旷的大坟场。巨大的灾难让活下来的人无法悲伤,一心只是想活着去救被埋者,去救受伤者,等待埋葬已逝者。这就是我第一眼看到的地震后的唐山,和触动我灵魂的灾后唐山人。大地仍在晃动,唐山的余震持续着,灾情依然不断出现……
主持人
《观察与思考》的第一个节目是《北京市民为何吃菜难?》,播出时间是1980年 7 月 12 日。节目审查通过后,职员表上我的职务应该怎么写呢?我们新闻部有记者、摄影师、编辑、编导等职务名称,写“记者”,不行,因为过去说的“记者”指的是摄影;如果叫摄影,不符合实情,因为摄影的任务只是拍摄,并不可能在现场采访,何况我们组有专职的摄影师。那么是不是可以叫编辑呢?可是叫编辑也不对,因为编辑是幕后人员。那么编导呢?叫编导也一样,他们可以现场指导摄影师拍摄,但没有出图像的任务或只为新闻写稿子、串编镜头,不可能自己出镜采访或面对观众报道。这可难坏了大家,没办法,只好把矛盾上交,请领导决定。
陈汉元与台领导研究后决定,叫“主持人”。我是第二天看节目播出时,新闻节目最后出的职员表上,我的职务写的是“主持人”,于是中央电视台的荧屏上,出现了过去从未在职员表上出现过的非常新鲜的“主持人”三个字,而我也就成为新中国电视史上的第一个电视台新闻性节目主持人。
大包干,我报道
滁州地委(滁县地区)研究室欢迎我们采访,并且向我们介绍了安徽滁州地区包干到户的情况。1978年安徽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大旱灾,省委书记万里提出把土地借给农民救灾。这个口子一开,安徽农村各地包干到户就暗中搞了起来。万里曾深入农村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凡是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都 增产,因此他态度鲜明地支持包干到户。但是对包干到户,各地还有争论,甚至中央也有不同意见。
我们并不相信他们说的,还是要看到实物才能肯定,于是进户查访。恰逢农历正月,正是农闲时期,人们大都在家过年。我们随便走进一户人家,屋中虽然比较暗,但是我突然感觉眼前一亮:一家人正围在桌前打扑克,桌子上摆着花生、瓜子等零食,惬意安适之感像一股暖流迎面扑来。这是中国的农村吗?眼前所见的农村和我在河北白洋淀农村看到的悲惨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
实行包干到户的地方,农民有了钱,希望孩子能上学读书, 所以对农村普及教育非但没有影响,而且还有了发展。有的农民买了手扶拖拉机,除了种地外用来跑运输赚钱。在县城或集镇,农民也开始办小企业,如“预制钢筋水泥梁”,满足农民盖房缺木料的需要;有的开面粉厂,帮助农民磨面,等等,农村经济开始活跃起来。调查所见,农村的变化给了我们报道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