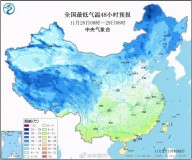风舞,原名朱国材,70后,浙江省诸暨市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诗歌作品散见《诗选刊》《星星诗刊》等。
风舞:用心建构诗意的家园
诸暨自古人杰地灵,书香浓郁。这里既是古代四大美女之一西施的故乡,又是著名画家王冕的故土。元末明初更是出了著名诗人、文学家、书画家和戏曲家杨维桢,他的《题春江渔父图》:“一片青云白鹭前,桃花水泛住家船。呼儿去换城中酒,新得槎头缩项鳊”,写得机智而富有禅意,读来令人回味无穷。近代诗人蒋智由,紫东乡浒山村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他与黄遵宪、夏曾佑被梁启超并列称为“近代诗界三杰”,有《居东集》、《蒋观云先生遗诗》等留世。
诸暨的诗歌土壤,是先贤用智慧和汗水翻新的。所以,只要播下一粒诗意的种子,稍加耕耘、松土,就会收获沉甸甸的果实。这些果实,可以是香榧、早稻,也可以是春笋、柑橘。
风舞无疑是诸暨诗人中,具有创作实力的诗人之一。
风舞的诗歌写得并不多,他属于灵感击中型写作,兴趣来了,或者说灵感来了,他就随着灵感的瞬间释放然后草书一首。很多时候,他是在思索写什么,怎么写,而当他静下心来与我们交流时,问得最多的却是写作的意义何在,如何让自己的诗歌辨识度增强,不至于重复自己,让诗歌的技巧和写作更上一层楼。看得出来,他正从一个成熟期的诗人向灵魂型的诗人过渡,在向内的审视和自我探究的过程中,他在不断解构诗歌与个人的内在联系。读风舞的诗,很容易在他诗行的字里行间寻觅到一种洒脱的、浪漫的、直率的抒情气息。他的诗歌,宛如骑士奔跑在草原仰天的怒吼,亦如一个多情的人面对尘世的繁华,独自徘徊在某处,低吟动人的谣曲。
比如《爱的蔷薇刺》,起笔时,写得很沉静:“疼痛安在红豆里/那抹深红在暗夜里微凉/浅笑安然 不想言语//围墙斑驳 岁月苍远/日子绕开我们的心情/好像开在路边的蔷薇/怀念渐行渐远的安静和美好//”,转折在这里:“你到底爱不爱我/只有受伤才能咀嚼阵痛/我要在梦里编织美好/或者以一场暗暗的哭泣/让爱情的故事跌宕起伏//蔷薇 其实我并不认识蔷薇/只是感觉这个名字的素雅/就像古代画中的女子/那粉红的花朵一定是微笑的/那嫩绿的枝叶是否有隐隐的浅刺/不得而知”,在这首诗中,诗人将一种矛盾的情感通过感性和诗性的语言表达出来,表面上写蔷薇刺,实则通过这一“诗眼”,将诗人对生命的、爱情的、哲学的思考渗透其中。在诗歌的空间里,我们看见了风舞诗歌的抒情品质,那就是激昂的感情、华丽的色彩、丰富的感觉,构成了一首诗岩浆般涌动的隐忍与震撼。
诗人、诗评家陈超在《诗艺情话》一文中说:“单就情感经验的提供而言,好的诗歌,或启人心智,或给人安慰,或让人活得更自觉;或抚慰你,使你觉得生命的困境是难以逾越的,我们不必再自我折磨。但所有这些指标背后,还有一个总指标,就是作者必得是一个有性情的、有语言才能的、有趣的人。无论表达什么,诗,首先要吸引人看下去,得有活力和趣味。无趣的诗,读几行就会厌倦,用不着读完。”
风舞的诗,给了我新鲜的阅读体验。在他激情的诗作里,我读到了他对生活和生命的热爱。比如:“那艘艰苦的老船已不受人控制/顺流而下迅捷不可阻挡/碎裂之声超过了江水咆哮/船的骨骼咯咯作响/刺透雨季、灾难、世事、穷富/表述的情形不是一个江南秀才能够描摹/只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方能体察”(《河床底下的老船》),在这首诗里,诗人赞叹的是古老的技艺,“船的骨骼咯咯作响”,这样的细节加重了诗歌的陌生化和诗意性表达,给人以无限的想象。
风舞的诗歌读得多了,愈发能够感觉到他用诗歌建构诗意的故土与家园的迫切性。从身份认同上来说,风舞的诗歌指向是没有明确指向的。他的诗歌选材和题材甄别看上去随心所欲,但是更多的是选取那些能够带来有层次美感的诗歌意象。他始终心怀谦卑之心,在诗歌里,深情地书写和揭示生活的真实与真情。他一直秉持“阅读陌生化”和“诗意立体化”的诗学理念。在汉语的美感之上,苦心锤炼自己的语言,力求让诗歌整体变得艺术形式丰富,艺术层次多样。不论是其早期诗歌还是近作,风舞都在自我营造的诗意家园里,安心打造属于自己的皇冠,这不是自我陶醉,从语言的成色和思想的成熟度上来说,他是想从内部的理性与思辨来表达内心的悸动与颤抖。
比如《后巷的蝉》:“你靠在后巷的木栏/守着那片蝉声啃食的树叶落下来/我还在远方的水上/挥汗如雨地划着七月/练习把鱼儿放生,照看船上的花//巷子深得像一个人烟稀少的峡谷/你在的时候,心中住着一座花园/货物丰盛,车水马龙/你不在的日子/满目雨重烟凉,柳暗梅青//我有时在杨柳岸骑马,射箭/腰带断裂,声音嘶哑/我有时从水中站起,身上挂满水草/月亮轻轻地移向西窗/你没有发现我伐木的声音/你在编织一个什么呢//河商盛传一个悲伤的消息/夏季的硅胶开始泄漏/就像一些陈旧的词语从语系中流出来/就像几只落单的蚂蚁/枯叶上的单蝗,噤若寒蝉//我知道那条青青的后巷/墨汁洇开,记忆是木栏上的绳结/你离愁的背影在雨雾中薄凉/翼瓣透明,失重一样飞起/我被官差挡在雎鸠唤醒的埠头”,这首诗是典型的“诗言志,诗言情”,诗人借助“蝉”这个意象来打开想象的空间,在这首诗里,诗人将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不论是“人烟稀少的峡谷”还是“我有时在杨柳岸骑马”,都是在营造一个浪漫的氛围,而这首诗也是在古典主义的意境和语境中,来安放一颗诗意的心。《后巷的蝉》在日常生活中捕捉到了诗歌的灵感,很好地还原了生活原生态的诗意与美感。通过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两相结合,产生了令人动容的生命之美,这份神秘感和对生命律动把握出来的感觉,是一个诗人内省与外放结合的人性守望。诗人试图将内心的诗意,通过汉语之美很好地传达出去。
而《梦境,秋水》则运用了超现实主义和古典主义相结合的写作方式,诗人写道:“梦中的草木是五彩和恍惚的/梳子的齿一样滚动着变幻的像素/我站在这个季节的悬崖之上/望见大河青青,无限的深度让我惊心/而你在大河之畔留连/你丝滑的长发也是青色//你看不见我声嘶力竭的呼喊吗/一定是喊破了对岸的稻浪/喊红了崖边的千秋叶/无限的不安惊出了隐在秋色中的烈马/咴咴地惊叫着奔突在原野/又忽地无声无息地隐去/我怕你那抹小小的身影/也要被马群扬起的烟尘湮没/像水中的墨迹一样散去//瞬间的焦虑形成一次内心的雪崩/裹挟着无数暗夜酝酿的芬芳滚落/下坠的时候我看见初秋的晾衣绳上/你编织了一年的草环温暖而平静/白色的板房粘满了记忆的草籽/请不要收走那朵风干的微笑/让飞鸟先回去吧好吗//我还是要回到文首的草木/流泪翻找你隐去的青丝/我要向兄弟借一辆轻捷的小车/在老板的案头放上我难以启齿的辞呈/骑行在暗哑的声带和泪腺深处/在黄昏飘落的青河边迎风而立/静待你从浅浅的潮声中走上岸来”,文题虽然写得是梦境,但是在梦境中,诗人却将想象力和感受力带来的美好体验全部运用到了诗歌的呈现上。“秋色中的烈马/咴咴地惊叫”,诗人在诗歌的美学里捍卫着古典形式的抒情传统,在现代主义的诗歌思想中种植汉语传统的表达与审美。读风舞的诗,需要结合着古典诗词的意境美去感受他诗歌中弥漫着的浪漫、唯美的气息。他的想象力带有着某种骏马奔腾的驰骋与辽阔,带有某种中国话的水墨诗意。有时,在他的诗歌中还能够感受到古典音乐的宁静与纯美,我想,诗人在写作时,是沉淀了内心的那份空灵。在《梦境,秋水》一诗中,诗人明显是带有理想主义的感情色彩进行写作的,在现实的烦乱与嘈杂的生活困境中,如何寻找解脱,如何安放诗意的心灵,如何去理出头绪,我想诗人在诗歌中都得到了合理地安排与书写。他在诗歌中埋下了一条秘道,这条秘道是诗人苦心经营的一个诗学思考。在呼唤人性美好与纯真的基础之上,打开视野里的宽阔与浩荡。“瞬间的焦虑形成一次内心的雪崩/裹挟着无数暗夜酝酿的芬芳滚落”,这样的表达,暗含着诗人脆弱而柔韧的心灵美。而“下坠的时候我看见初秋的晾衣绳上/你编织了一年的草环温暖而平静”,更像是自语时的某种解脱。我能够感受到诗人在这首诗里所要追求和追寻时,对自己个体命运挣扎时的那份苦痛。诗歌的表意是唯美的,但是诗歌的内在却是带有某种隐痛的。
风舞的诗歌澎湃着诗人的激情,但又不是激情直白的抒发。诗人洛夫主张诗人通过意象化的处理,来让激情冷却,通过意象,来增加诗味。T.S.艾略特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诗不是情绪的表达,而是情绪的逃避”。洛夫更是补充道,诗歌是节制的抒情,是诗人把情感深深地渗入事物之中,再透过具体而鲜活的意象表达出来。这种表达是情与景的交融,意与象的结合,一经融会,景物便充满了生机,无情世界变成了有情世界。回头看风舞的诗,他在意象的筛选上,有着独特的心得。
比如《荆棘鸟》,开头是一种细致地描述:“父亲的地头总有一只荆棘鸟/毛色炫丽,眼神气派/不鸣不叫看护着地下的芽尖/向下汲水,向上取光/让种子在暗夜将晓的时候拱土/催促绿叶从父亲的眼中摊开/风和日丽地生长//我会在阳光下背一桶汗水/像荆棘鸟一样去逡巡田地/顺手浇灌,拨去纠结满脑的野草/我坐在田埂与长带豆的藤蔓对话/昨日的雨水梳理了豆荚的心思/那些结籽的苋菜满腹忧愁/它们即将告别农夫的手掌/岔小芋终会被上级的公文扼杀/为的是确保主线的根正苗红//”,诗歌写到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到诗人心中澎湃的激情和热情,在对童年的追忆,和情感的铺陈过程中,他在寻找一种寄托的方向:“我没有注意那小鸟的鸣叫/抑或是远山的风声穿过荆棘的尖刺/再者地头的溪流击打着午后的平庸/我听不见它刀割一般的绝望/无法体察它毛管树立起惊涛骇浪/在小小的身躯内排山倒海/扑闪的翅介于飞腾和惊恐/在春天的时候荆棘尚且娇嫩/它是要拉长日子,延缓刽子手的刀锋//在父亲的田埂读荆棘鸟/我看到年轻的梅吉身姿绰约地行走/目光飞向每一扇神秘的窗户/织针左右碰撞出喋喋的声音/神父把一粒火花射进少女的心/比任何事情都危险,迷人/圣经里的油汀滋滋地响着/克利里的焦虑长得像一组陈旧的沙发//鸟的飞扑是为了激活那根悲怆的唱针/而拉尔夫的教堂穹顶纠集了最大的电阻/像乌云中密布了阻止往生的机关/教袍的权力掩盖不了人性的虚惘/我宁可在漫山遍野的蝉鸣里/为荆棘鸟编织一个柔软的谎言/设下鲜花盛开的陷阱,诱惑爱情进入/合理的射程。让梅吉的歌声/在我父亲的溪边婉转如霞”,诗人借助“荆棘鸟”这个意象,展开联想,叙述了童年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对“梅吉”美好形象的描摹与感怀。风舞在写这首诗歌时,他一定是将思绪放飞到了童年的某一个时刻,在诗意的展示时,不仅从容而且舒缓,像“延缓刽子手的刀锋”、“为荆棘鸟编织一个柔软的谎言”,这样的传神而细腻的细节书写,让我想到了叶朗的“必须要人的意识去发现它,唤醒它,点亮它”。风舞的诗歌如水银泻地般流畅,但仔细去回味,却又会让人不断地去思索时间与空间编制的人间,诗人的个性该如何显露,情感和思想世界该如何呈现。风舞的诗歌是在展示一种传统美学的力量,是在展示激情化为冷隽的意象后,情感的深度剖析。他在给诗赋予中永恒的艺术生命。
读风舞的诗,要去发现他诗歌中营造的深度意象,诗人本身是在让客体与本体达到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在纷繁的语言系统中,他在构筑自己的精神领地。风舞的诗,源于生活的深层次思考,坚守诗歌创作的古典美感。读他的诗,你能读到一颗诗心的高雅与淡泊,他恪守着内心的善良和纯真,遵从于心灵的呼唤。他的诗歌,安静、沉实,富有自然的清韵。抒情诗优雅的,也是冷静而敏感的。在这扎实、绵密、有纹理的诗句背后,他的笔总是伸向别人不易觉察的地方去探索,去发现。看得出来,他的诗歌写作更加接近于一种情感的经验表达。
梅尧臣说:“诗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意。内外意含蓄,方入诗格。”许多诗人不约而同地把心灵性、心灵力量看作诗歌的重要特征。诗人白连春更是认为“每一首诗都应该是心灵的慰藉”。读风舞的诗,你能从细腻的情感背后,看到一个诗意空间所散发的诗歌的阳光。在有节奏的诗歌语言和秩序中,季振邦的诗作,常常给人以留恋的美感。这份美感宛如披着外衣的江边少女,那懵懂的初恋,正要寻觅的,恰恰是内心包裹的一颗敏感的自然诗心。
诗歌不是杂文式的批判,不是散文式的抒情,也不是小说的虚构。它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诗歌有着自己的写作轨迹和文学脉络。风舞的诗歌写作,在诗与现实之间,找到了一种美学的平衡。他用他自己的冷静、节俭、舒缓、深刻的解读方式,去诗歌的海洋中,寻觅属于他自己的浪花。这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和表达。在诗性意义上,他不断地超越自己,也不断地否定自己,去突破,去蜕变,去圆满地寻求诗歌的轮回。
读风舞的诗,不能停留在诗歌语言的表面,而应该读懂他诗歌背后所要表达的深刻的含义。他的诗歌中,有着巨大的悲悯情怀,也有着对自然嫁接的本真深入。他的诗歌艺术风格,注重发现和感受,在平常的事物中,让诗性去抵达精微的细节。然后借助诗歌的力量,客观、从容、冷静地从自己的情感中,取出藏匿的感动和瞬间。他的诗歌,对精神的复杂性和语言的弹跳力有着节奏上的控制。
阅读风舞的诗,还有另外一种阅读的惊喜,就是这种细节中所呈现的爆发力。他的诗歌,宛如开山凿石的人,挥动着臂膀,拿起锤子和錾子,向着石头坚硬的质地,砸下去,溅出火花与碎石。他在用词语唤醒诗歌中沉默的情感,用意向表达着内心的激情与赞叹。他的诗歌,很好地深入一个人的情感深处,去寻找深埋已久的感受和秘密。风舞一直在坚持有难度的写作,他在微信上经常给我发一些诗歌新作,看得出来,他的作品,总是在向着更高难度的山峰去攀登。这是一种高难度的诗歌理想主义。值得尊敬。

王利锋,80后,浙江文学院青年作家(诸暨)班学员,诗歌作品散见《星星》《江南》等。
王利锋:构建纯净而朴素的诗学观
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的写作语境中,微信平台(包括微信群、朋友圈、公众号等)的拓宽增加了诗歌发表的途径和渠道,为增强诗歌的传播和加速诗歌向公共方向的转移,提供了便利和可能性。诗人们变得不甘寂寞,一天一诗者有之,一天数首诗的创作也很多。创作主体的情感表达太过激情澎湃,其生产出来的诗歌,值得怀疑。
所以,我对诗歌的阅读还停留在纸刊上,我以为,纸刊的制作周期要长,其编辑的审核也更为仔细和认真,阅读起来,触觉和视觉的结合,更富有诗意。而在这读诗的过程中,最欣喜的莫过于读到自己喜欢的诗。我喜欢的诗,有以下几个特征:一、诗歌的语言朴素、平实,不花哨,最好是日常的用语,准确地语言叙述,让语言自身呈现诗歌的力量;二,与我个人的生命经验贴近,这样有助于理解诗歌内部的奥义,或者表达的不同人生经验中有新的发现,且能让我感受到诗歌的美以及触摸到诗人诗心的纯真;三、复杂、歧义、新奇且难忘。
王利锋的诗,是我喜欢的诗。
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在意象选择上和语言表达上,都有其独立的一面。王利锋的诗,受西方诗歌的现代主义影响较小,他还是比较倾心于汉诗所追求的汉语性,在诗歌中保留了古典的诗韵以及汉语所散发出的独特的抒情气息。他将个人经验以及本土表达还有现代诗学观,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王利锋的诗歌有其自己独特的风格,蕴含着朴素的人生智慧。
比如《秋天的树》,这首诗强化了自己诗歌的地域符号,那就是“老台门”,在《回来,离开》《小满》两首诗中,“老台门”在诗中也被提到过。写诗就是表达心灵的感受,不论是抒情也好,还是叙事、记景,都是内心有所触动,然后记录下那份震颤的感受。《秋天的树》,表达了对外婆的一种怀念,诗人将外婆拟物化比喻成“和春天消失的雨水一起/长成了一棵秋天的树”,然后让情感漫溢,展开对“秋天的树”的联想。这首诗情感控制的很好,节奏也很有层次,读起来能够感受到诗人在诗歌中沉淀的真情。
《西施》和《东施》都有借古喻今之意。写这类诗歌,最重要的是对典故的熟悉,以及化用典故时,能够将个人经验渗透其中。在素材的筛选和意象的提炼上,也更向外,是一种由表及里的写作形式。本身这两个人物都与诸暨有关,身为诸暨故里的诗人,对这两个人物的诗意化处理,也在情理之中。王利锋写出了自己的诗歌特色,写出了内心对待女性人物的同情、怜爱和关怀。
《太阳花》似乎是一首青春的谣曲。借“太阳花”表达了对“姐姐”的怀念。这里的“姐姐”似乎是一个虚指,指向是远方或者诗人脑海中那个向往的地方。借物抒情,托物寄情,这是诗人常用的写作手法。这种对命运不确定性的描述,以及对现实世界芜杂生活的悲叹,有的时候显示的不仅仅是悲观的气息,更是一种长久的无奈和一种深情的向往。
《回来,离开》《谷雨》《地平线》等都是怀乡之作,说实话,这些年,我读得最多的诗歌就是怀乡类的诗歌,但是读了这么多的诗,遇到怀乡类的作品,还是忍不住要多读两遍。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骨子里的“怀乡情”。尤其是当下,工业文明和城市化的推进,让乡村变得几近模糊,我们记忆中的故乡已经不复存在,怀乡诗保留了这份记忆,尽管是在文字里,但也足够真切。荷尔德林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一句话道出了诗人内心保留了最后一丝真情。这三首诗,语言清新,没有生僻字词,读起来也不会有太多的语言障碍,但是反复阅读几遍,又能感受到不一样的诗意。
关于诗歌写作,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诗歌就是想象。一首好诗,首先他要能触动读者的心弦,让阅读诗歌的人在第一时间被诗句所打动,继而产生强烈的共鸣和认同感。诗还应该是自然的,真挚的,不虚假,不做作,不拿腔作势,不哗众取宠。诗更应该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在岁月的流逝中,它的光芒还能够风采依旧,它的诗句还能够熠熠生辉,我觉得这就够了。诗是不能用‘好’来评价的。和其他任何美好的事物一样,它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是能消除内心一切丑恶欲念的心灵之良药,是能够让人不断反思和修正自己思想的灵魂标尺。我觉得诗是客观存在的。它就像宝玉一样,深埋在每个诗人的心灵深处,等待着诗人的挖掘。好诗是天然的瑰宝,是自然生成的,不需要任何打磨和雕琢,不需要任何的修饰和装扮。好诗就是真善美的因,结出的果。”
今天读来,这段话,依旧能引发不小的共鸣。王利锋的诗,纯净、朴素,他在追求他自己诗歌的最好最高的抒情方式和法则。之前有的人问我,每个人写诗的风格都不一样,如何判定一个人的诗歌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或者如何在一众诗人中判定诗歌的好坏高低。虽然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是文学创作必定有着它自己的规律可循的。比如,是否形成了自己的语言特色,是否让诗歌更加贴近心灵,在自己的诗歌创作道路上,有没有自我重复和炒冷饭,还是持续不断地增加困难写作,写出有新意的作品,这些都是诗人应该时刻扪心自问的。
王利锋的诗歌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兰波说:“诗歌就是赋予抽象观念以具体可感知的形象”,当我们在王利锋的诗歌中,感受到语言带来的美好阅读感受,我们更应该深入诗人的内心,去了解诗人内心对诗歌写作的本能坚守。比如《麻雀》《眼泪》《我需要》,我前面已经说了,诗歌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而作为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诗歌往往又是经验、形式和语言三者的有机统一。如何让语言变成自由的精神创造,拒绝陈词滥调、虚伪造作,如何让形式上有新的发现,让自己的个人经验更准确地在诗歌中进行表达,这是诗人需要毕生追求的。回过头来,我们看这三首诗,诗人正在将情感一丝一丝的抽离出来,形成一种欲语还休的留白,让更多地想象变成一种诗意的空间,然后让读者去感悟。
读王利锋的诗,我的脑海里总会闪现他的身影,青春阳光,儒雅温和,满身的书卷气息,却又能够平和如水波。王利锋骨子里保留了古代书生的安稳与沉思,他的诗歌也如同他本人一样,真诚而简单。但是在这里我想提醒王利锋的是,那就是诗歌的写作不像学生写作文,有模板可套作,有形式可复制。诗歌写作的终极是展示人性,展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形式上更是要求要求变求新,不断挑战自己,什么样的形式都可以尝试着去写,然后让情感变得更克制,将个人经验与生命经验结合时,要追求人性的复杂和精准。有时候,我们活在俗世之中,很难免要面对俗世生活的复杂一面庸常一面,而诗人写诗,就是要用诗意来对抗复杂和庸常。
王利锋正在构建自己纯净而朴素的诗学观,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一定能够找到他自己的诗歌天空和诗性世界。

何大金,本名何新乐,诸暨新锐诗人。
何大金:还原事物的本真
读何大金的诗,是要颇费一些脑筋的。如果没有读过现代派的诗歌或者没有现代派艺术理论做支撑,读他的诗就会很难进入他诗歌中的自由心境,以及象征、隐喻所隐藏的讯息。十三首诗,我一首接一首的往下读,靠前的诗歌都没有抓住我的眼球,倒是这一首《路边樟树下》,让我眼前一亮。这首诗的出现,让我再折回头,重读前面的诗作,大有别开洞天的阅读感受。
顾城说:“写诗总在神会之时,读诗又何尝不是?神会而得意,得意而忘形,是诗的至境。诗有神方为好诗,而好诗无神硬读也成滥调。因此我告诫自己,诗不要专门读,于神会便好。”
读何大金的诗,让我不得不重提那段老话:“诗歌之美源于自由:心灵的自由,精神的自由。”一个诗人,只有心灵上获得彻底的自由,他写出来的诗句才能够轻盈地飞翔起来,才能够呈现出独特的气质和个性。诗人最忌讳淹没在人群之中。失去个性的诗人,无异于断臂以示众人。何大金有一颗敏感的诗心,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他是用思考来捕捉灵感的诗人。亲近光明,传递良善。葆有一颗悲悯之心,且审视内心的视角细腻而灵动。
这组诗歌更像是诗人的独白。通过细微的发现还原事物的本真,用本真的生命之光折射诗心的温暖。像《塔》《今晚》《自由》等,抒情的基调从起句就开始表明自己的态度,一直在探寻,一直在叩问。他在诗歌中不断追求灵魂的自我救赎之道,是真诚而激昂的在寻找。且诗歌中有朦胧诗的抒情风格,保留了八九十年代的自由抒情之风。他对自身的生命体验,有着敏感地认知,对于事物观察也更具深度。像“高塔耸立,指向天空/黑夜白天大地上/一枚静默的针,指向天空/狂风怒吼,它不为所动/鸟声婉转,它不为所动/它仅有一种姿势/一种信念/定要刺破这虚无天空/然后在废墟之上/放声大笑……”,情感真挚,诗句中有美好的人性之光在闪耀,也更有阳刚的父性气息在弥漫。看得出来,诗人受西方现代派诗人的诗风影响较大,他的诗歌中有金属的声音,更有直入心灵的力量。
在这里,我要着重谈一谈《路边樟树下》和《一个呆子》。《路边樟树下》,全诗一共十四行,但是诗人叙述平静而沉稳。诗歌语言,清新、自然,没有前面几首诗有意的“口号式”表达。就是老老实实叙述,自然地呈现生活的真实场景。其实,这样的生活场景,我们几乎每天都能遇到。估摸着,也曾想把它写成诗歌,但对语言的驾驭力度不够,对诗意的提炼欠缺,对事物的观察缺乏仔细的研判,于是,放弃了。何大金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表达出了我们想表达的。尤其是“行人们也都匆匆/为各自的生活燃烧着分秒/只有不远处的环卫工人/不紧不慢在清扫落叶/累了他就停下来/把自己倚在扫把上闻闻花香”,就像一幅画面,把一个温情的场景,再现在脑海。这首诗需要细品,慢慢回味,就像顾城说的,需要心领神会。
其实,优秀的诗人,对语言、意象和情感的处理,是非常从容且冷静的。诗人和语言的关系,就像剑客和剑、刀客与刀的关系。刀光剑影之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剑客和刀客心中的侠气以及内在的力量。汉语是一个巨大的熔炉,我们要把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思考的内容放进熔炉,然后提炼出自己想要的句子,这个过程,考验一个诗人对词语具有的尖锐而深刻的驾驭能力。诗人不能回避现实,不能逃避自己内心脆弱的一部分。相反,有时必须真心坦露,把事物本真的一面,原原本本呈现。丑恶的一面也好,良善的一面也罢。越是立体的呈现,越是出好诗的绝佳时机。在诗歌中,开辟出自己对诗歌观念的认同,达成普通事物诗意化,诗歌语言的符号化。直至最终,让人生经验和艺术经验,在诗歌中,创造性的融合,方为诗人的情感达到心灵回归的至上法则。
而《一个呆子》较《路边樟树下》这首诗要弱一些。但是从诗歌的完整构成上来说,是成立的。《一个呆子》和前面的《刷牙》构成了一个立体的意象。《刷牙》里没说完的话,在《一个呆子》中表现出来了。当生活经验与生命经验融合在一起,我们看见了某种思辨的永恒。何大金更像是一个在场者,在做现场直播,或者说现场叙述。他的诗歌边界,圈定在某个特定的范围。让诗意从个体生命出发,感受真实的力量。
何大金的诗歌中有批判意识,有对现实的批判,有对诗意的个性化解构,也有对个人心境的自由化表达。他在语言的把握上,有着自己的写作秩序。在追求语言张力和悲悯情怀的同时,让诗歌在艺术的形式上,尽量做到丰富而有情韵。
这一组诗歌中的不足之处,有的地方在表达上显得过于直白,比如《自由》一诗,直接地陈述,主题上表达出来了,但是含蓄的诗意被口号式的表达冲淡了诗味。不论是西方现代派的诗歌技巧,还是古典诗歌的意境化用,都强调含蓄之美。意象,其实就是诗歌的诗眼,就是一个可以隐藏的诗歌因子,能够撬动整首诗呈现立体美感的单词。而意境本身就是一种更高级的含蓄之美。诗人写诗,不是泄私愤,不是为自己的私欲寻找发泄的方向。个性化表达,是发出自己的声音。诗人的定位,是美的化身,是爱神恩赐的对象,诗歌是一种美学,是一种美折射出的丰富形象。
正如诗人顾城所说:“要找出诗人和别人的不同之处的话,有一点,就是他有一种虔诚,他希望自己变得透明、通达,好让光能够清澈地通过;如果他是浑浊的话,光就通不过。让光通过他——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如同常说的自我拯救。”通过写诗,我们能寻求到一种圆满。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是失意者,面对命运的种种不公,或者怀才不遇,或者生活不顺心。但是在诗歌中,在写诗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用一种更高的境界提升自己,让自己暂时脱离现实,得到精神上的升华。从而与现实世界达成某种互补。写诗是一种修行,是一种潜在的对自我人格再塑造的过程。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诗心变得澄澈一点,更澄澈一点。写诗时,让诗句含蓄一点,更含蓄一点。就像溪流,水质是至纯至净的,但是流速是缓缓流淌的,是有声音的悦耳的流淌。这些话,和何大金共勉,和诸暨众诗友共勉。

司徒无名,本名王科峰,90后,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入选第六批浙江省“新荷计划”人才库。
司徒无名:怀旧是一首无言的诗
诗人潘维在诗集《水的事情》谈到写诗,说:“这一问题追逐了我许多年,直到剥开洋葱,让每一片都摊开。最初是源自一种想表达的欲望,其实可以说是个体生命在寻找社会意义,他在时间的茫茫人海里寻找自己的那张脸;再进一步,美学企图产生了,也就是说希望用语言炼金术,拯救出某些人性的纯真;最后抵达,每首诗都是一场文化仪式,用来调整灵魂的秩序。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有着更云端的答案:命运。是命运驱使我做一个诗人。”
司徒无名和我是浙江文学院青年作家诸暨班的同学,我对他的诗歌应该来说很早就读过。司徒无名的诗,在抒情的诗意中,动用了隐喻、象征等手法,他的诗歌,有很强的精神承载能力和艺术形式上的拓宽空间。在这一组和少年情怀的诗歌中,按照潘维的阐述,他的写作介于追寻生命意义和美学企图的提升之间。司徒无名借助诗歌来完成精神上的沉淀和修行。诗人并不是天生就存在的,是命运的选择,是自我的指摘,更是灵魂的诉求。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读司徒无名的诗,就像是在翻阅他用心素描的人生册页。
比如《落叶或信》,借落叶来表达内心的怅惘,回到故乡,回到父亲的土地,看着父亲一天天变老,内心泛起的波澜。诗歌的语言,很清新,排比句用得恰到好处,还有对意象的提炼,也比较清新和集中。《故乡或梦》则是直抒胸臆,回到故乡,回到那熟悉的梦境或现实,然后像一个孩子一样,行走在回家的道路上。《黑夜》和《平衡术》有着生活的某种隐喻。《那个喝醉酒的男人》和《墨恋》《沦陷》还原了生活的一个瞬间。《替身》《过路人》《孤儿怨》,有个人明志时,内心的一丝悸动。
我想从司徒无名的诗歌出发,谈一谈诗歌对于我们有何现实或者虚无的意义。就我个人而言,我读诗,是在和诗人进行心贴心的交流。我们为什么写诗,就是对抗庸常的生活,在诗歌的诗意与诗境中,寻觅那份悠然,安放栖息的灵魂。现实生活一地鸡毛,诗歌的空间里,可供喘息,总有文字能够理解我们内心的孤独。而当完成这份心灵的初衷时,我们融入到了诗境之中,就是想达成某种心灵上的安慰。不再是语言游戏,不再是宣泄,不再是工具,诗歌就是诗歌,它指引着我们,可以攀登进入信仰的殿堂,可以成为一种美学的启示,还可以达成某种生命的联系。
可以理解成和潘维阐述文字的唱酬。
90后的司徒无名,他的这一组诗歌是在处理内心的怀旧情绪。怀旧本身就是一首无言的诗。是怀旧的情绪让我们靠近真实,让我们放下虚伪的装扮,放下无谓的思绪,只有本真的自己,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他开始书写故乡,书写熟悉的生活细节时,我们发现,他在诗歌中寄托的实际上是我们大部分人共通的情感。潘维说,是命运驱使我做一个诗人。对于司徒无名来说,何尝不是怀旧驱使他写下这一首又一首的诗。怀旧是命运的一部分,命运中自然有怀旧的情绪萌动。
司徒无名的诗歌创作,一直是在一种灵感支配的情况下进行的诗歌写作。他和诗歌的关系,若即若离。这让我他的诗歌,像《墨迹》《沦陷》,就有一种眼前一亮的语言新鲜感。且,在处理语言和意象的关联上,他也试图在找到一种舒适的处理方式,让语言的感觉,更生动。和诸暨的其他诗人相比,司徒无名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都并非循规蹈矩那种,渗透进诗歌当中,自有天马行空的想象。诗歌是诗人的声音,是美学的彰显,期待司徒无名能继续保持这种锐利的感觉,发现更多诗意,然后提炼,写出佳作。
——以上评论摘选自诸暨市文联《浣纱》文学双月刊,具体诗歌参见各期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