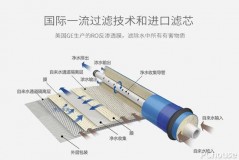根据绿妖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少女哪吒》
原生家庭是我与生俱来的厚壳,用了我十几年去凿穿。理解父母的过程,也是理解自己,像用打火机去融化一座冰山。
文/绿妖
“我们现在怎样做子女”是一个危险的题目。家庭中的角色,如果需要学习也应该是父母。做父母不需要执证上岗,而中国人许多有潜在的精神创伤,为人父母后,造成子女童年阴影的概率之大,从豆瓣人气小组“父母皆祸害”的活跃可略见一斑。所以,近一百年前鲁迅发表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并未过时。
如果父母没问题,我们现在应该不需要讨论“怎样做子女”,需要讨论,则证明源头出了问题。另外,“怎样做子女”很容易和 “孝道”呼应,变成对子女的单方向要求。在昏暗的集体无意识中,“孝”之一字,仍然有着模模糊糊然而一呼百应的群众基础。下跪给父母洗脚、背诵《弟子规》,这些戏码背后的塑造之手,也令我恐惧。
我想讨论的是,在有问题的原生家庭中长大的子女怎样重建人生。像一场慢性病,从跟父母决裂到和解,我用了十多年。有的人是情感专家,有的人是恋爱专家,有的人是育儿专家,而我,是父母专家。
亲人互为对方的刽子手,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这不就是尤金·奥尼尔的戏剧?
曾经有几年春节我很怕回家。刚毕业时,父亲反对我去北京,召集了我所有的姑父来我家开会,把我围在最中间讲道理、斥责我。没见过世面的我,无意间觉得牙齿微微相磕,然后发现自己全身都在抖。发抖着,不服,不松口。所有男性长辈拂袖而去后,我和父亲相互说了决绝的话。
然而最难克服的是,他放弃后陡然的老态和无奈,像一团暮色一样坐在沙发中。发抖着,拖着箱子,离开家,像用一把刀割断一条过分长、过分结实的脐带。伤口在刚到北京的头几年一直发炎。
那几年,总有一种站在悬崖边的心态,因为背后无路可退。很小的事也不能失败,一点点失败都让我觉得马上会粉身碎骨。第一次谈恋爱,我只有一个渺小的愿望:只要我还能跟一个人保持长久的亲密关系,就能证明我是正常的——理所当然地,我没能保住那段感情。

《如父如子》中两个抱错小孩的家庭面临着血缘与亲情的纠葛 。 图/《如父如子》剧照。
那些年的春节,每回一次家都是一次火山爆发。积攒了多年的怨气,人又都到齐了。有一年,我刚进家,箱子还没来得及拎到卧室,父亲和姐姐不知为何吵起来。我去劝架:“别吵了,大过年的,你们就用这个欢迎我回家么?再吵我可走啦!”
没承想,并没有人要给我这个面子,父亲当即指着我:“你走,你立刻走,你马上走。”我很有志气地拎起箱子走到院子里,昂起头,好像在看天会不会下雪,其实是尴尬地不知道该去哪里。
当时还没有高铁,我坐了一天的车,进门已是傍晚。天色将雪未雪,彤云低锁,山河凋零,正是林冲夜奔之光景。我呆呆望天,直到被我妈拉回屋里。接下来的战况更加惨烈,父亲砸了家具,一地玻璃渣,他光着一只脚,一边像一头落在陷阱里的老熊般在屋里走来走去,一边哀号。滚在地上的饮水机嘶嘶向外喷水。姐姐用小板凳砸自己的头。
我坐在我的(一直没机会拎上楼的)箱子旁,困惑地想这不就是尤金·奥尼尔的戏剧:亲人互为对方的刽子手,所有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我们把对方下台的台阶拆掉,拆得干净利索,一点余地没留。所有人只能在激烈的情绪上往下走,走到底。

由西德尼·吕美特执导的经典之作 《长夜漫漫路迢迢》改编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同名自传戏,讲述了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从早到晚所发生的各种碎残纠结之事。图/《长夜漫漫路迢迢》剧照
那些年的春节,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情况。有时和缓点,有时激烈些,但从未风平浪静。所谓甜蜜的家,所谓避风的港湾,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能懂的是“逼疯”而不是避风。
也是在那时,我在“父母皆祸害”小组潜水,看到了更多惨烈,更多的尤金·奥尼尔。
暴君式的父亲,控制欲强的母亲,我无法体会他们内心的恐惧。
要到一定年纪,才能懂得自己的遭遇并非孤例。身边朋友多数和父母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它们超出了普通家庭事务的范畴,带着浓重的心理创伤。
杜拉斯笔下最好的角色是她的母亲,一个执意筑造堤坝以抵挡太平洋的女人,绝望而疯狂。为她的悲剧命运加持的,是没落的殖民地中没落的穷白人这一史诗背景。而我的朋友的父母制造悲剧的能量之大,也足够滋养一部伟大的小说或者电影,在他们给周围投射的阴影里,影影绰绰跳动着一个时代坚硬的血管。
暴君式的父亲,控制欲强的母亲,令人发疯的(多半是关于吝啬的)怪癖,沿着这些共性回溯,我看到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的成长:在多子而缺乏关注的家庭中长大,在该上学的时候没有上学,该发育的时候挨饿。
恐惧和丛林法则式的自我保护成为其生命的底色,培养一段健康亲密关系所需要的细腻情感、包容以及最重要的情绪管理,他们都匮乏。
中国是礼仪之邦,在印刷术不普及的时代,一位老者就是一部礼仪字典,是家庭和邻里纠纷的调节者及裁决者。然而在当下,“老人”这个词变得令人愕然:跟年轻人大打出手抢篮球场、摔倒后碰瓷扶他起来的好心人、带着幼儿肆无忌惮地在国内外街头大小便……他们的情绪无法自控,犹如孩子一般。
放眼望去,那一代人中的一部分,心智的某一层面似乎永远停留在了饱受惊吓的童年,在成年后,还被那个儿童控制着他们的人生,敞开着索要补偿的无底洞。
父母几乎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十几岁时以为他们不爱我,二十多岁试图理解他们是怕花钱,三十多岁的现在,微信视频已经不花钱了,他们还是很少联系我。母亲偶尔会,但是父亲从不。这几年我打回去时,有意识地点名要跟父亲也讲一会儿。刚开始他很局促,讲不了两句总想挂断。后来我跟他谈他的身体,他的冠心病,他的锻炼方式,我们的话题多了一点点。
但总是我问,他答,像用打火机去融化一座冰山。他主动提及的话题只有一个:你说话小心点。父亲不是文人,一辈子当工人,爷爷也只是一个蜂农。但是那一句话透露出他的恐惧从未消失。
我没有经历过漫长的挨饿,没有长达几年挣扎在最基本的生存线上。我无法体会他们内心的恐惧。
理解他们的过程,也像用打火机去融化一座冰山。

《少女哪吒》小说中有句话——"她像哪吒,剔骨还母,彻彻底底自己把自己再生育一回。只是她能力有限,没办法把自己养育得更好。"予人深刻的印象。
所谓孝顺,其实是有技巧的爱。
转折点来自支教的那一学期。当我尽了全力,仍然被马蜂窝般的课堂逼疯时,我在崩溃中变成一个让孩子们害怕的老师,放学后我一个人在山坡上站到天黑。只能原谅自己了,我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而只是一个能力有限的普通人。
忽然也理解了父母。和课堂上崩溃的我相比,他们生我的时候更年轻。两个普通男女的育儿生涯做得顾此失彼,千疮百孔,如果给子女造成了童年阴影,成为一个让孩子害怕或失望的父母,也并非他们的初衷吧。
当我以童年阴影受害者自居时,在“父母—子女”的关系中,我仍然执童年视角。父亲随口一句斥责足以令我全身紧张,进入战斗状态。那一刻,我是在父母狂暴的争吵中无助哭泣的小孩,是14岁还被父亲用皮带抽得羞耻得想死去的少女,我不是现在的我,一个30多岁、拥有许多沟通技巧的成年人。
理解他们,从受害者的位置离开,成为家庭关系进入下一阶段的开始。父亲再说什么,不会轻易刺激我。“水瓶座说话就是这么毒你有什么办法”,我用星座消解父权。很奇怪地,当我不再反应激烈,父亲反而很少再对我说什么难听话了。
沟通技巧很重要。刚毕业那几年,父母总嫌弃我春节回家的装束,我以为是嫌憎我不舍得花钱,恰巧那几年我真的很穷,这种猜测简直万箭穿心。直到几年前,我才明白他们嫌弃的是我的缺乏娇艳,永远的黑大衣。进而可能还会焦虑穿成这样的我,何时才能嫁掉。这太简单了,有的人为了父母连春晚都愿意上,穿身红衣服对我何难?以前我是有多自我,才不懂这里头的人情世故?
以及,所有非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员工的朋友一定要有清醒的自我认识,这些职业之外的工作对于父母来说,都是没有工作。更不要提自由职业,那会让他们焦虑得半夜坐起。自由职业的我,这几年,刊登有我访谈或者文章的报刊,以前不留的,现在都寄回家里。隔三岔五,电商淘宝礼物不断。杀手锏是带父母出国旅行一趟,一举证明我的财务实力、生活自理能力。不知是否心理作用(我觉得不是),从那以后,父亲对我说话客气多了。
妈妈说我很孝顺。不是的,这是有技巧的爱。

和父母沟通也需要一些耐心和技巧。图/pixabay
要打破轮回,就必须停止向外归因,对自己的缺陷人生负起责任。
最难的是从受害者的位置离开。童年的经历会变成性格的一部分,与你同行。比如我恐惧改变。因为害怕变动,害怕跟陌生人打交道,我的生活一直做减法,直到四五天不出门成为常态。极简的尽头是与世隔绝,是生命的干涸。
经过学心理咨询的朋友的提醒,我发现,自己在每件事的最初都会想到最坏的结局。我想起小时候每一次的改变都变得更糟。童年的结束,从父母整天吵架开始:他们不吵了,他们离婚;不要离婚,不要吵架,不要改变。类似这样的经验成为你的生命底色,对你之后的人生持续地发出指令,让你三十多岁的时候变成一个害怕出门的废柴(如我)。
从迹近命运的力量下逃离是最难的。我有一千个理由原谅自己,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我与生俱来的基因,这是我的性格,这是我的宿命,我能有什么办法。就像我长成一个不给家人打电话的人很正常,反之,养成给父母打电话的习惯,却要做很多心理建设。
但是要打破轮回,就必须停止向外归因,对自己的缺陷人生负起责任。这很难,但并非不可能。就像即使从未得到过父母无条件的爱的人,也努力给自己的孩子以无条件的爱,健康的爱,自己从未得到过的爱。打破轮回,就是给出你之前也没有得到过的:信任、包容、理解,爱与理性的光明,给父母,给你亲密的人,给这个世界。

《千与千寻》里父母因为贪吃变成了猪,千寻只能踏上拯救自己和父母之路。图/《千与千寻》剧照
假如父母并不理解我们,我们为何要尝试理解父母?因为我不要被心里那个饱受惊吓的儿童控制,接续上那条流淌着戾气、阴郁之血的坚硬的血管,在60岁时成为另一个无法情绪自控的老儿童。在“父母—子女”关系中,我不再是无助的等待被拯救的孩子,而是一个成年人对另一对成年人。理解他们,我才能更好地过自己的生活。
理解他们的过程,也是理解自己,像用打火机去融化一座冰山。
所以我讨论的不是“如何做子女”,而是,一个成年人可以怎样面对自己的童年阴影。但我并不提倡“子女一定要与父母和解”,看过许多惨烈案例,想获取父母欢心的子女,被后者以亲情要挟,全面控制,压榨殆尽。人性的黑暗深不见底。
我们能不能接受,一段亲密感情,很有可能是既爱且恨的,爱和恨并行存在、相互独立。既认可自己恨的正当性,也包容爱的存在。承认贫瘠扭曲中也有爱存在,不代表为发生过的贫瘠与扭曲正名。最后,不强求自己必须和解,因为自己也是有局限的普通人而非圣人。

学会面对自己的童年,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图/pixabay.com
我说过,原生家庭是我与生俱来的厚壳,用了我十几年去凿穿。不断重新审视,不断有新的发现,像在黑暗的房间摸索,一面厚墙、一段起伏的弧形、四根柱子,终有一天拼凑成一头完整的大象。这样反复确认是消耗,但也是我的成长。
但愿新一代的年轻人,这篇文章的读者们,不需要这样的成长。
,